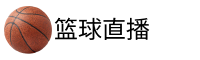讀初敬業先生的畫作,直覺是:元氣充盈,生機蓬勃,像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正在興旺時期”。
我曾請教過初先生:為什么喜歡畫牦牛?他的回答是:來自對青藏高原的感動。那片被稱為世界第三極的高原為什么能夠感動他?因為那里有他敬仰的曠遠、深邃、博大、清潔、堅毅和質樸。作為一位畫家,在這個時代,他將高原所蘊藏、所彰顯的精神本色視為他繪畫藝術的追求,而最能代表高原精神的象征物,就是雪山、曠野和牦牛。于是,雪山、曠野和牦牛就成為初先生抒發心聲的載體,成為他表達內心感受的藝術符號。
大多數畫家都能根據個人心性及偏好選擇創作主題,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意識地、自覺地理解描述對象所承擔的詩情畫意及其哲學內涵。畫家能否對某一特點的象征物做出獨特的、精致的藝術再現,并以個人化的筆墨給予美學闡釋,是很難的。對情感之寄托物的藝術再現不是簡單的擬物,不是對既有存在的臨摹,而是給予迥異于他人的、近乎唯一的敘述和理解。初先生筆下的牦牛有三個特點:雄健——不是唯唯諾諾的、逆來順受的家畜,不是一般的耕作動力,也不是招徠游客的工具,他筆下的牦牛是自由的、狂放的、健美的符號,并因此擁有了獨特的詩意。其次,他筆下的牦牛都是富于動感的。奔跑中的動物比呆立不動的,要難畫得多,前者擁有運動的邏輯,許多元素因移動而發生變化,不是那種專門等人描摹寫生的模特兒牛。即使凝立于荒山大雪中的靜態牦牛,也能看到與大自然抗爭的生存意志,讓人感嘆生靈的倔強與堅強。三,初先生的牦牛,不論是單個的還是成群的,都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它們立于曠野,那是堅實的大地,以此道出牦牛與天地的關系。它們成群結隊,縱橫馳騁,依托遠方的雪山和無際的高原,從那里發現和描述牦牛的精神。咆哮的江河為牦牛發出聲音,無邊的草原闡釋著萬物相互依存的哲學要義,渾然一體,給人以自由奔放的啟發。
以上三點,不是所有畫牛的人都能做到的。
初敬業先生是大學美術系教授,兼通中國畫和西畫。他對歐洲藝術不僅有系統深入的學術功底,其油畫作品既別致,也很精美。2019年,我曾在福瑞德美術館和濱河西岸一家畫廊欣賞過他的油畫作品,心生欽佩。他筆下的形象(如女人體)都是經過大膽的藝術處理,角度微妙,筆觸肯定,以相當獨特的方式展現了人體的美。我由此聯想到現代藝術史上的一種觀點:現當代許多重要的藝術家大都兼備中西畫修養,技能扎實,視野開闊,而且注意融合不同藝術元素使之成為個人獨特性的營養。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我以為:藝術需要多重營養,需要兼收并蓄,需要廣集博取,這樣才能成長得更健康。其次,正因為不同形式的藝術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沖突,讓藝術家找到了創新的激情、切口和路數。
藝術營養的雙重性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畫給予人的是內斂、詩意和情調,還有獨特的筆墨技法。西畫講究造型、透視和色彩,給人帶來更強強烈的質感、更微妙的細節,更融合的色彩,還有中西藝術都很講究的結構關系的相互性。于是,那些兼備中西繪畫技能的畫家不僅獲得(或說繼承)中國文人的筆墨趣味、情感寄托和結構的恬適感,也獲得了西方文化崇尚的自由奔放、情調個性以及講究標新立異的志趣。有了這些元素的滋養,此類畫家往往會展現出視野寬闊、游刃有余、筆墨瀟灑的特點,也因此避開了蒼白、老舊和重復。
藝術家找到托物言志的愛好并不難,但要形成風格,則不易。這里既需要學識,需要悟性,甚至需要天賦。我覺得,初敬業選擇雪山牦牛和他的個性氣質多少有些關系。他豁達爽朗,對人充滿善意,堅毅而質樸,這樣的人選擇雪山、曠野和牦牛作為托物言志的符號,是適宜的。客觀上說,過去的四十年,各種不同藝術風格在中國得到介紹和推廣,自由和開放為畫家提供了寬松的環境。初敬業是一位真誠而且明亮的藝術家,他對繪畫充滿熱情,積極參與當代生活,努力將藝術分享給社會,而不是蜷曲在個人情趣中自憐自嘆的小畫家。同樣的時空并不能讓每個藝術愛好者都成為優秀藝術家,這里有價值追求的區別,有筆墨悟性的高低,也有個人志趣的選擇,等等。豁達開朗的個性,全面的專業技能,豐富的人生經歷和高遠的審美旨趣,造就了初敬業先生現在的藝術風格。初先生正在興旺時期,他的藝術前途是光明的,遠大的。
初敬業作品雅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