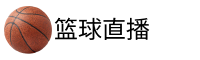我們早已習慣算法為我們的選擇指引方向。然而,當機器能毫不費力地生成我們所消費的內容時,人類的想象力還剩什么空間? 本文刊登于2025 年 9 月 1 /8 日合刊的《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After the Algorithm.” 作者:約書亞·羅斯曼(Joshua Rothman)是《紐約客》特約撰稿人,也是每周專欄“開放問題”的作者。他自2012年以來一直在該雜志工作。 若人工智能繼續將創意工作自動化,文化“產物”的總量必將大幅增加。新的文化形式,或是現有形式的新用途,會將我們引向始料未及的方向。 視覺設計:大衛·紹德;由人工智能生成 我常常在黎明前醒來,比妻子和孩子們都早,只為能享受片刻獨處時光。我輕手輕腳走下樓,來到寂靜的廚房,喝一杯水,戴上AirPods耳機。接著選首音樂,啟動咖啡機,然后坐下靜靜聆聽,等待咖啡煮好。 正是在這種半夢半醒的狀態下,我與算法的“邂逅”開始了。昏昏沉沉中,我會在Reddit上刷些適合為人父母者看的內容,或在YouTube上看攝影視頻,又或是查看蘋果新聞。廚房島臺旁的筆記本電腦在召喚我開始工作,我也確實想接受這份“邀請”——但要是一不小心,我可能會把某部沒看過的電影的所有片段都看完,或是點開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警察題材劇集《菜鳥老警》。這部劇講述一位中年父親通過加入洛杉磯警察局重塑自我的故事(我是在TikTok上發現這部劇的,或許是因為我和主角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相似)。最糟糕的情況是,孩子們醒來時我還在刷手機,而我為爭取這一小時獨處時光所放棄的睡眠,也白白浪費了。 若這樣的清晨場景讓你覺得似曾相識,那是因為進入智能手機時代已有數十年,生活的節奏與算法的節奏早已交織融合。我們穿衣服時聽播客,睡前刷網飛(Netflix)。白天的間隙里,公交車上刷Bluesky社交平臺,健身時用Spotify聽音樂,午餐時看Instagram,晚餐前刷YouTube,刷牙時看X平臺(原推特),失眠時逛Pinterest。這樣的生活方式頗為奇特。算法其實由來已久——公元前300年左右,歐幾里得就發明了求兩個整數最大公約數的算法。本質上,算法是解決問題的數學步驟。我們用算法協調實體事物(如電梯),也用它處理行政事務(如醫療住院醫師分配)。可將零散的空閑時間視作一個“待解決的問題”,這種做法合理嗎?我們用算法“解決”了它,如今卻連片刻空閑都沒有了。 算法化生活帶來的一個后果是過度刺激,另一個則是我們思想上的某種混亂。我們為何會在意那些我們在意的事物?在黑暗中走進地下室,你可能會撞上蜘蛛網;有一種哲學觀點認為,“在意”的產生就如同這般——在生活中,我們會被那些偶然出現的可能性所“纏繞”,陷入一張張“在意之網”。清晨偶遇年邁的鄰居,當晚便會牽掛他過得如何;上中學的孩子喜歡查佩爾·羅恩(Chappell Roan)的音樂,久而久之你也成了她的粉絲;13歲時偶然讀到《源泉》,或許會讓你成為終身自由主義者。算法文化利用了我們分配“在意”時的隨意性與偶然性——它借助這樣一個事實:今天偶然接觸到的事物,或許會讓我們在明天為之著迷。而與此同時,編織這些“網”的機器,歸企業所有。 長久以來,我總覺得自己被困在個人的“在意之網”中,難以掙脫。直到去年的一個清晨,我懷著試驗的心態,在黎明前的廚房里與人工智能系統克勞德(Claude)開始對話。咖啡正在煮,我在手機上輸入:“我正在寫的文章終于有進展了。” 系統回復:“早上好!這真是個好消息——當你一直在打磨的文章開始有眉目時,那種感覺太美妙了。這篇文章是關于什么的?是什么讓你取得了這樣的進展呢?” 我沒有回復。無論在那個時間點,還是其他任何時候,我都不想讓人工智能充當我的寫作指導。但既然已經用了手機,我索性把它放下。抿了口咖啡,我開始修改之前的草稿。 之后的清晨,我仍會和克勞德、ChatGPT聊天——不過聊的不是我的寫作,而是我感興趣的話題(為什么關稅不好?地鐵里的犯罪問題是怎么回事?暗物質為什么是“暗”的?)。我不再查看蘋果新聞,而是開始問Perplexity——一個基于人工智能的網絡搜索系統——“今天世界上發生了什么事?”它總能給出簡潔的新聞摘要,信息量足且不啰嗦,有點像《經濟學人》雜志里“世界要聞”(The World in Brief)那欄的風格。有時我會追問,但更多時候,我沒有進一步閱讀的欲望,而是拿起一本書。我發現,人工智能也可以很“無聊”——這種技術特質,此前我從未留意過。 巧合的是,大約在同一時期,由算法驅動的互聯網世界——也就是Reddit、YouTube、X平臺這類平臺所在的世界——開始失去吸引力。2018年,記者馬克斯·里德(Max Read)在紐約提出過一個問題:“互聯網上有多少內容是虛假的?”他指出,很大一部分網絡流量來自“偽裝成人類的機器人”。而現在,“人工智能垃圾內容”似乎正在接管互聯網。整個網站的內容看似都由人工智能撰寫;人工智能生成的模特有著千篇一律的美貌,耳環的位置卻奇怪地錯位;發布在網絡論壇上的軼事以及下面的評論,都帶著聊天機器人特有的語氣。有研究發現,網絡上超過一半的文本都經過了人工智能修改,越來越多的“網紅”似乎完全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警惕的用戶開始信奉“死亡互聯網理論”——這種曾被視為陰謀論的觀點認為,網絡世界已經完全自動化了。 1950年,計算機科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控制論(研究機器、生物體和自動化系統如何自我控制的學科)的創始人——在其著作《人有人的用處》中提出,現代社會是通過“信息傳遞”來運轉的。他寫道,隨著社會規模擴大、復雜度提升,社會事務在更大程度上會依賴“人與人造物之間、人造物與人之間,以及人造物與人造物之間的信息傳遞”。人工智能機器傳遞和響應信息的速度遠快于人類,數量也遠超人類——這是引發擔憂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個原因是,當這些機器以直白、怪異、狹隘,甚至完全錯誤的方式傳遞信息時,我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將其融入自己的生活。部分正因如此,維納后來寫道:“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場愈發艱巨的斗爭,對抗我們自身智力的局限,而非一張讓我們舒舒服服躺著、等待機器人奴隸伺候的吊床。” 我們身邊的信息正在發生變化,甚至能“自我撰寫”。從某種角度看,這些信息似乎正在讓過去二十年來那些受算法影響、試圖影響和控制我們的人類聲音變得沉默。在廚房里,我享受著這份寧靜,卻也因它而感到不安。這些新的“聲音”會告訴我們什么?而留給我們發聲的空間,又還剩多少? 不久前,為了給兒子彼得辦七歲生日派對,我在搭一個巨大的雙峰后院帳篷時拉傷了背部。因此,我在動感單車上鍛煉的時間變多了,去舉重房的次數則少了。一天早上,把彼得送到夏令營后,我騎著虛擬單車在瑞士湖畔的路徑上“騎行”,同時聽著埃文·拉特利夫(Evan Ratliff)的播客《騙局》(Shell Game)。在播客中,他用人工智能模型模仿自己的聲音打電話。盡管我們對播客的沉迷,反映出我們時刻都想消費媒體內容的需求,但播客仍是算法生態系統中一片寧靜的“島嶼”。我常常在整理房間時聽播客。短時間干活時,我會聽《歌曲解析》(Song Exploder)、《鏡頭作品》(LensWork)和《與格雷琴·魯賓一起更快樂》(Happier with Gretchen Rubin);要做的事比較多時,就聽《 radiolab 》、《埃茲拉·克萊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或泰勒·科文(Tyler Cowen)的《與泰勒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Tyler)。我喜歡這些播客里的觀點,也享受這種“陪伴感”——有格雷琴和她身為編劇的妹妹伊麗莎白“陪著”,洗碗都變得更有趣了。 播客的魅力在于情感的真實性:耳機里傳來的聲音,仿佛是房間里的三位好友在與你交談。也有人嘗試過完全自動化的播客制作——Perplexity曾推出過一檔名為《每日發現》(Discover Daily)的播客,內容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科技、科學與文化深度解讀”——但這類播客往往缺乏吸引力,也沒有思想深度。《 radiolab 》的聯合主持人拉提夫·納賽爾(Latif Nasser)告訴我:“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發掘和提出創意。”在《 radiolab 》的辦公室里,使用人工智能是“禁忌”——納賽爾說,這“就像越過警戒線一樣”——但他“出于好奇,會問人工智能,比如‘給我提五個播客選題’。我想看看它能給出什么答案,結果那些選題都很糟糕。” 不過,要是你給人工智能提供優質的原創想法呢?或許通過自動化制作,這些想法能變成實實在在的作品。去年秋天,我的播客列表里新增了一檔名為《深度探索》(The Deep Dive)的節目——每一期都是我用谷歌的NotebookLM系統生成的。制作一期節目時,你只需將文檔上傳到在線資料庫(即“筆記本”),然后點擊一個按鈕。很快,一對男女播客主持人就會用逼真的播客語氣,討論你上傳的任何內容。NotebookLM本是一款研究工具,所以我第一次嘗試時,上傳了一些科學論文。但主持人那種刻意營造的“感興趣”,并沒有真正讓我產生共鳴。后來,我把自己正在寫的回憶錄中的幾個章節傳給人工智能,效果好了一些——聽著主持人給出的“見解”很有趣,起初聽到他們給出正面評價時,我還挺有成就感。但真正讓我覺得“對味”的,是嘗試用自己多年前寫的、有些已經忘了的文章來制作播客。 討論我幾年前發表的一篇散文時,其中一位主持人說:“這是個很深刻的問題——直擊核心。” 另一位主持人接著說:“這個主題很有野心。” 我在廚房水槽邊忍不住笑了,邊聽邊洗早餐的碗碟。一開始,我只是覺得有趣——將一種為大眾消費設計的內容形式,用來服務“只有自己一個聽眾”的場景,這種體驗很新奇。但更有用的是,它讓我想起了自己過去的想法,其中有些觀點現在我或許會修正。 若人工智能繼續加速創意工作,或讓其自動化,文化“產物”——播客、博客文章、視頻、書籍、歌曲、文章、動畫、電影、節目、戲劇、辯論文章、網絡人設等等——的總量將會增加。但由于人工智能有其獨特的優勢和不足,“更多”并不一定意味著“更多同類事物”。新的文化形式,或是現有形式的新用途,會將我們引向始料未及的方向。納賽爾告訴我,他曾發現ChatGPT能快速寫出一篇有趣的短篇故事:以他年幼兒子最喜歡的元素“硼”為主題,模仿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的《好心眼兒巨人》(The BFG)的風格。“元素周期表”與《好心眼兒巨人》的結合,此前沒人提出過這樣的創意,但一旦有了這樣的作品,我們或許會發現自己其實很喜歡。 當然,這并非真正的“合作”。當兩個人合作時,我們期待他們的個性碰撞出火花。而人工智能沒有個性——而且,由于它最核心的能力是識別模式,其“合作成果”往往會固化所融合內容中模式化的部分。更關鍵的挑戰在于,人工智能缺乏藝術能動性:必須有人告訴它“什么是有趣的”。所有這些都表明,人工智能文化可能會將人類的原創性淹沒在大量缺乏動機、千篇一律的“藝術”海洋中。 然而,自動化也可能為新視野的表達創造機會。“AI或消亡”(AI OR DIE)——一檔自稱“首個100%人工智能制作的喜劇小品節目”——的匿名創作者之一“思維旺克”(Mind Wank)告訴我:“我有獨立電影制作的背景,干這行很久了,后來停了下來。”當Runway這類人工智能視頻工具出現后,他得以將那些未被制作或無法制作的想法付諸實踐。如今,他和另外兩位合作伙伴——團隊成員分別位于加拿大、美國和波蘭——制作的暗黑超現實主義喜劇視頻,已擁有數十萬觀眾(在一個典型片段中,名為“小腳踝”(Lil Cankles)的Twitch主播在玩一款叫“自助洗衣店”的游戲。“ lint 溢出來了!”一個電腦合成音尖叫著,同時大量 lint 從烘干機通風口涌出)。旺克談到自己的合作伙伴(他們也都有傳統影視行業背景)時說:“我們能有現在這點優勢,原因在于我們懂電影語言——我們了解燈光、鏡頭、膠片。” 在他看來,傳統電影制作是線性的:“有了想法,先寫成處理方案,再寫成劇本,然后找人、找投資。之后才能從前期制作進入拍攝階段——這過程太麻煩了——九個月后,還要在剪輯室里努力挽救自己最初想法的‘殘片’。”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允許在任何階段進行無限次修改。他說,每月花幾百美元,人工智能工具就讓他實現了“年輕時只能夢想的創作生活。現實世界中的限制太多了,而現在,我可以創造全新的世界。”這項技術讓他想到了“六七十年代的作者電影文化”。 整個團隊從未見過面,但他們頻繁交流,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創意“泡泡”里。波蘭籍合作伙伴本特·蒂貝特(Bengt Tibert)告訴我:“畫畫時,你身上會沾滿顏料味;開始寫提示詞(給人工智能的指令)后,我連做夢都在想提示詞。這就像開啟了新生活。”蒂貝特解釋說,睡前他會構思一個提示詞,醒來后就把夢中想到的內容寫下來。 加拿大籍合作伙伴“博伊”(Boey,僅用單名)也表示:“我的腦子幾乎一半時間都在電腦里。” 如今的人工智能視頻工具,會在細微處暴露其“機器屬性”,形成一種易于識別的風格,而且制作短片段時效果最好。但這些工具正在快速改進。旺克說:“我在等這些工具達到足夠的穩定性,能讓我們用固定角色制作一整部故事片。”到那時,人們就可以用它們制作一部完全常規的劇情片或浪漫喜劇。“我們都熱愛電影制作,熱愛電影藝術,”他說,“我們有想拍的電影、電視劇,還有廣告。” 蒂貝特說:“現在能實現的想法太多了,時間卻不夠用,這幾乎讓人不知所措。” 我是在兒子的房間里和“AI或消亡”團隊通話的,為了躲開他的小妹妹。通話結束后,我合上筆記本電腦,環顧房間里兒子的東西:他在兒童陶藝工作室做的杯子里,裝著五顏六色的夏普創意馬克筆;一本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涂色書里,有復雜的動物圖案。他已經涂完了一頁:一只羽毛蓬松的鸚鵡站在鐵絲網前的樹枝上,他用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顏色,創造出一幅色彩斑斕的畫面。嚴格來說,這樣的作品是“衍生性”的,屬于“填色”類。但它遠不止于此——原創性,正是在“模式化”的背景下顯現的。 下午,我要和幾個老朋友吃午飯。25年前上大學時,我們一起上過創意寫作課。我們的教授——著名同性戀小說家、回憶錄作家埃德蒙·懷特(Edmund White)——最近去世了,其中一位朋友在切爾西街區的達拉斯燒烤店組織了一場小型紀念聚會。二十多歲時,懷特有時會和我們一起在這家店吃晚餐。 走路去餐廳的路上,我用語音模式和ChatGPT聊天,問它這個街區的歷史。它用“活潑好奇”的人設——一個名叫瓦爾(Vale)的英國女性——回答:“當你沿著第八大道在29街到27街之間行走時,就來到了切爾西街區的核心地帶。這里歷史上以繁榮的制造業和服裝業聞名。”它還提到,“切爾西有許多LGBTQ+酒吧、社區中心和活動,是紐約市LGBTQ+文化的重要陣地。” 我說:“其實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長的紐約人。所以我想知道一些我可能不知道的、真正有意思的事。” 人工智能試著用一些關于“錫盤巷”(Tin Pan Alley)的趣事取悅我——其實錫盤巷的位置比我當時所在的地方偏東一點——還有20世紀初樂譜行業的經濟情況。我問起第七大道上一棟外觀奇特的建筑,人工智能稱它“是該地區豐富建筑和商業遺產的見證”。 我要求道:“別用‘這棟建筑為街區增添了活力’這種陳詞濫調和泛泛之談。”我建議,或許可以聚焦一些更“聳人聽聞”的事實。很快,我們就聊到了南希·斯龐根(Nancy Spungen)的謀殺案——1978年,她在切爾西酒店100房間被刺身亡。她的男友、性手槍樂隊(Sex Pistols)前貝斯手希德·維瑟斯(Sid Vicious)被指控謀殺,但案件尚未開庭,他就因海洛因過量死亡。 到了餐廳外,我拋出一個冷門的房地產開發問題——切爾西的建筑為什么都不高?——這場對話聊不下去后,又問起看到別人T恤上“我愛紐約”(I??NY)標志的背景故事。人工智能向我詳細介紹了設計師米爾頓·格拉澤(Milton Glaser),以及20世紀70年代標志誕生時的社會氛圍(當時有“福特對紐約市說:自生自滅吧”的說法)。“你想看看原始草圖嗎?”它問。我正猶豫,就看到一個朋友從街對面朝我揮手。 從一件事聊到另一件事,再到下一件事——在這種轉換中,人工智能的能力堪稱出色。在《銀翼殺手2049》里,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飾演的角色下班回家后,與由安娜·德·阿瑪斯(Ana de Armas)配音的人工智能女友喬伊(Joi)聊天。窗外下著雪,音響里卻播放著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夏日微風》(Summer Wind)。“你知道這首歌1966年發行于復興唱片公司(Reprise Records)嗎?”她平淡地問,“當時還登上了排行榜榜首。”她穿著“鼠幫”(Rat Pack)時代的蓬松連衣裙,為一道菜譜發愁——隨后,為了迎合男友變化的心情,又換上了一身緊身黑色套裝。片刻之后,兩人來到他公寓的屋頂,共享浪漫時光。與人工智能系統聊天,就像是在“表演”一個實時撰寫的劇本。即便劇本枯燥,其快速修改的能力也可能被誤認為是“自發性”或“活力”。某個事物能隨著你將話題從音樂轉向謀殺,再轉向米爾頓·格拉澤——或是從烹飪轉向調情,再轉向戲劇——而始終跟上節奏,這或許會讓人覺得它擁有“思維”。 這種流暢性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意味著什么?藝術作品有其特定形態(3分鐘的流行歌曲、三幕劇)和特定情緒基調(喜劇、悲劇、浪漫、哀傷)。但當不同形態、情緒和形式之間的界限如此容易被打破時,這些界限還能穩固存在嗎?硅谷先驅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他助力發明了虛擬現實技術,現就職于微軟——告訴我:“現在人們都在討論,人工智能對內容創作者是好是壞?但‘內容’這個概念本身可能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實時合成內容’——其設計目的就是對接收者產生影響。”如今,Spotify上已有人工智能生成的歌曲,但至少這些歌曲還會標注(虛假的)樂隊名稱。拉尼爾說:“未來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人們提到‘音樂’,就只是‘音樂’而已。”在這種未來場景中,當你登錄人工智能版的Spotify時,“聽到的第一句話會是‘嘿,寶貝,我是你的Spotify女友。我給你做了個播放列表,有點性感,別在別人面前聽哦’。”這個“播放列表”里的歌曲,都是前所未聞的,也可能不會再被聽到——它們是在當下為你量身定制的,或許基于人工智能觀察到的你的個人情況。 拉尼爾認為,長遠來看,各種文化體驗——音樂、視頻、閱讀、游戲、對話——都可能源自一個單一的“人工智能樞紐”。屆時將無需向創作者付費,而樞紐的所有者將能對受眾施加極大影響;正因如此,即便有些人不想以這種方式體驗文化,他們使用的應用程序也可能朝著人工智能驅動的方向發展。 文化具有群體性——我們都喜歡成為“欣賞者社群”的一員。但拉尼爾說:“如果計算成本足夠低,就有可能創造出‘社會幻覺’——你得到的是量身定制的體驗,卻會誤以為自己在和一群人共享這種體驗,其中有些可能是真實的人,有些則可能是虛擬的。”(我不禁想象,這就像喬伊把高斯林飾演的角色介紹給她的“朋友”們認識。)他接著說,要身處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分離社會”,“人們必須做出改變,但人是會變的。我們已經讓人們習慣了虛假的友誼和虛假的愛情。道理很簡單:這基于人們的欲望。”如果人們對某樣東西渴望至極,有些人就會愿意接受次等的替代品。拉尼爾神色凝重地說:“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也不是在預測它一定會發生。我認為,把這些可能性說出來,能增加它不發生的概率。” 在餐廳里,我和朋友們回憶往事。我們的教授埃德(Ed,埃德蒙的昵稱)講課風格輕松,甚至帶點八卦色彩——他會聊自己認識的人,也會聊自己喜歡的書。他自己的小說風格親切,像日記一樣:故事往往以這個街區為背景,似乎取材于他在這里的生活。他肯定也給我們講過敘事技巧和其他寫作相關的建議,但幾十年過去,那些內容已經模糊;如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曾討論過《單身男子》(A Single Man)和《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還有他曾稱贊過我穿的一件襯衫,以及他曾詳細描述過“為什么有些人在派對上很無聊,而有些人很有趣”。 那些研討會和晚餐時光,讓我們覺得文化世界——真正的文化、紐約的文化、藝術家的文化——觸手可及。但這個文化世界究竟是什么?它不只是一份“待體驗藝術作品清單”,盡管清單也是其中一部分。它本質上是一個在師生、繆斯與詩人、標桿人物與打破規則者之間展開的故事——所有人都在與文化形式博弈,而這些文化形式本身也在不斷演變、延續、衰落、破碎、融合、重生。你必須先理解這個故事,然后用自己的創作“融入”其中。 午餐快結束時,我們的話題轉向了愛情。其中一位朋友,在“得克薩斯巨杯”瑪格麗特酒的作用下,滔滔不絕地講起她和未來丈夫共度第一晚的火辣故事。 “我不知道為什么要跟你們說這個。”她說。 有人提議:“我覺得埃德會說,你應該把這個寫下來!” 我心想,與真實個體憑借真實生活創作的、充滿獨特細節的藝術相比,那些無限生成、形式散亂、缺乏背景和個性的“人工智能文化”,根本毫無意義。但隨即,我想起了自己過去黎明前的日常——一首歌聽到一半,一部電影看些片段。1980年,學者米歇爾·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探討了人們如何“櫥窗購物”、如何略讀文章而不細讀,以及如何在“受限”的通勤時光中尋找觀察和反思的機會。在他看來,人們通過“重新利用”自己的世界,在一個試圖塑造其情感、思想和抱負的系統中,為自己開辟空間。按照這個邏輯,當你制作一張混合歌曲的CD送給心儀之人時,并非在說“你的迷戀由這些歌曲定義”,而是在表明“你的情感比任何一首歌都更豐富”——你在用這些歌曲創作屬于自己的、更宏大的作品。 那么,送一張人工智能創作的混合音樂CD給心儀之人,又意味著什么?或許,我們仍能從自動化藝術中為自己創造意義。一首“無人創作”的動聽旋律,依然動聽。流行明星在某種程度上本就是“產品”,但圍繞他們形成的粉絲社群卻無比真實。然而,文化不只是被消費的對象——它是人們在生活中創造的產物。我們欣賞“創作行為”,也珍視“自然感”。電影觀眾在為電腦特效驚嘆的同時,也開始欣賞“實體特效”;人工香精的存在,讓天然香味更受歡迎。探索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化,或許會讓我們更加珍視那些“只有人類才能創造的文化”。 2023年,我為《紐約客》雜志撰寫了對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的人物專訪——他有時被稱為“人工智能之父”。像這樣的采訪結束時,我總會有些傷感。幾個月后,懷著懷舊和好奇的心情,我把那篇專訪輸入ChatGPT,說:“寫一篇關于其中人物的同人小說。”系統先是生成了一份“讀書報告”,分析它從中識別出的觀點、人物和寫作手法,然后附上了一段敘事文字。故事開頭是:“午夜時分,杰弗里·辛頓站在木制碼頭上。 頭頂上方,夏末的夜空沒有月亮,卻異常清澈。銀河像一片發光的大腦在天際鋪開——無數星星聚集成神經突觸般的圖案,一個由閃爍連接構成的宇宙。杰夫(杰弗里的昵稱)抬頭凝視著……身后的小屋一片漆黑。記者喬希(約書亞的昵稱)當天早些時候已經離開,在駛離的船上向他揮手。四天的采訪,像攪動池塘里的沉淀物一樣,喚醒了杰夫記憶中的往事和想法。如今水面重歸平靜,但有些東西已經改變。” 故事快結尾時,話題轉向了人工智能。辛頓“睜開眼睛,對著夜空說道: ‘我不怕你,’他輕聲說,‘我怕的是我們會用你做什么,或是沒做到什么。’他的聲音消散在水聲中,‘我怕的是我們自身的缺陷,會在你身上得到映照。’” 我覺得這個開頭還不錯。但在接下來的章節里,人工智能把故事引向了驚悚片的方向——虛構的辛頓要應對一個失控的危險模型——卻沒能營造出任何真正的緊張感。作為一名作家,我反而松了口氣。驚悚片本該讓人“脊背發涼”“心跳加速”“不寒而栗”;我想,或許一個沒有身體、沒有自我保護本能的系統,無法傳遞這些感受;又或許,人工智能難以掌握創作優秀懸疑作品所需的邏輯布局。創作故事的挑戰,其實有很多種。電視劇編劇卡莉·門施(Carly Mensch)——她與人聯合創作了女子摔跤題材喜劇《美女摔角聯盟》(GLOW),也是納賽爾的妻子——笑著告訴我:“我對‘情感投入’很挑剔。我認為,構建一個能讓觀眾‘投入情感’的故事真的很難,而懸疑情節反而可能很容易。” 故事形態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在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標。故事必須顯得“自然”,卻又要包含引人深思的觀點;情節轉折要出人意料,組合起來卻要形成清晰易懂、令人愉悅的結構;要有明確的“利害關系”,同時又要足夠豐富,能讓不同人從中找到樂趣。創作過程很少一帆風順。門施說:“很多好想法都源自無聊、錯誤和意外。在編劇室里,過程其實很混亂,大家會拋出很多想法。有時,一個‘錯誤’的想法會引出正確的方向。當你能說出‘這不是我想要的第二章’時,你就學到了東西。”(聽到這里,我不禁想,人工智能提出的糟糕故事想法,或許也能派上用場——比如作為一種“自動化頭腦風暴”。)在最高水平的創作中,好故事既要“映照”受眾,又要“改變”這種映照。關于敘事,有兩種理解:一種是“田園式”的,門施引用她曾師從的一位教授的話解釋道:“每個部落都有講故事的人,夜晚圍坐在篝火旁,我們站起來,向部落講述部落的故事。”另一種是“戲劇式”的:“你走進一間黑暗的房間,然后被眼前的一切驚艷。” 人工智能能創作出在所有這些層面都讓我們滿意的故事嗎?或許不能。但故事不一定要達到這種完美程度。在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6年的小說《零伯爵》(Count Zero)中,一個女人回到家,連接上神經接口,然后用長達六小時的時間“沉浸式觀看”一部名為《重要人物》(People of Importance)的長篇肥皂劇,“徹底放松大腦”。這部劇的“復雜情節”無需有始有終——關鍵在于“持續播放”,而非“結局”。同樣,我們個人的“人生故事”也未必符合“優秀敘事”的標準,卻依然讓我們無比著迷——因為我們身處其中。如果每個人都有專屬作家——就像古代的宮廷史官——或許我們能將“自拍”的潮流進一步推向“以自我為中心的敘事”領域。(打開元宇宙(Meta)的人工智能應用,你可能會看到的第一個選項就是“聊聊我的一天吧”。) 在彼得的生日派對上,我試戴了一副雷朋元宇宙(Ray-Ban Meta)智能眼鏡——外觀和普通眼鏡一樣,內置了人工智能界面。我環顧后院,最終目光落在一張陰涼的桌子旁:新搬來的年輕鄰居夫婦正和我岳父坐在一起。彼得在吃冰淇淋蛋糕;孩子們揮舞著泡沫劍和水槍,在草坪上追逐打鬧。 我問:“元宇宙,你看到了什么?” 眼鏡通過我耳邊的小揚聲器回答:“一群人坐在帳篷下的桌子旁,天氣很好,大家一起享受美好時光,看起來像是家庭派對。真不錯啊!”那種感覺,就像有人“共享”了我的大腦——看到我所看,聽到我所聽。 我抬手碰了碰鏡腿,眼鏡拍了張照片。這副雷朋眼鏡是我兒子朋友的媽媽艾里斯(Iris)的。她說:“我喜歡問它問題,比如‘迪迪(Diddy)案有什么新進展?’”開車時,如果家人聽的音樂她不喜歡,她可以私下點自己的歌。她拿出手機,滑動瀏覽派對上拍的照片——這些照片通過無線同步從眼鏡傳過來,記錄的是她視角下的后院。“第一人稱敘事”——關于“你”的故事——是人工智能已經能熟練講述,或幫助你講述的領域:或許用于心理療愈,或許用于回憶往事。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政策主管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曾說,他把日記條目輸入公司的系統克勞德(Claude);人工智能讓他意識到,自己尚未完全消化“成為父親帶來的形而上學沖擊”。通過這種方式,人工智能或許能“講述”我們的故事,甚至“修改”它們。 幾年前,關家永(Daniel Kwan)聯合執導的電影《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斬獲七項奧斯卡獎后,這位導演對人工智能產生了興趣,并利用自己新獲得的知名度,與人工智能領域的從業者會面。關感到震驚的不僅是人工智能可能給電影行業帶來的顛覆,還有它可能對“故事在社會中的傳播方式”產生的影響。在他看來,那些試圖向廣大觀眾講述引人入勝故事的電影,在“算法化生活”面前本就舉步維艱。他說:“我們的溝通體系已經完全斷裂,注意力被分割得支離破碎。”而人工智能可能會讓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 在西村一家餐廳喝咖啡時,關問我:“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是什么?可以說,不是互聯網,也不是農業,而是‘系統性、制度性信任’——正是這種信任,讓我們得以構建社會。而這種‘構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集體故事——上帝、政府——這些故事讓我們把彼此視為同一個家庭、同一個社群的成員。現在的技術,就像讓我們在玩‘疊疊樂’(Jenga):我們從底層——從‘集體認知’和‘對共享世界的信念’這個基礎——抽走積木,用來搭建更高的部分。如果繼續這樣做,整個塔都會倒塌,我們將退回到‘只信任部落中150人’的狀態。” 在《瞬息全宇宙》中,楊紫瓊(Michelle Yeoh)飾演的第一代美國移民埃弗林(Evelyn)發現,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龐大的“多元宇宙”中——在這個宇宙里,現實和“自我”的所有可能形態都存在。來自另一個宇宙的丈夫告訴她,他們的女兒喬伊(Joy)在另一個宇宙中,因意識到“單一現實的無意義”而陷入瘋狂。這個“另一個喬伊”信奉虛無主義,決心摧毀整個多元宇宙。埃弗林也曾一度陷入瘋狂,但隨后她有了存在主義頓悟,說服“邪惡喬伊”:唯一的出路,是選擇擁抱“你在這個特定宇宙中所擁有的特定的人”。 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把它當作一個移民故事(我母親和楊紫瓊一樣,在馬來西亞長大,她總被“如果當初”的想法困擾:如果當初留在馬來西亞會怎樣?搬去倫敦呢?定居西海岸而非東海岸呢?)。后來,隨著劇情推進,我看到了它對“算法化社會”的批判——在這個社會里,我們被大量“和自己很像,卻比自己更優秀”的人的形象包圍。現在,我覺得它預見了一個“人工智能充當個人‘山魯亞德’(Sc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的講故事者)”的世界:它會無休止地講述關于我們自己和他人的、可隨意修改的故事,把我們拉入一個個“平行現實”,遠離我們本可共享的“真實世界”。 關說:“看看我們面臨的所有危機——氣候變化、兩極分化、共識性真相的崩塌、收入不平等,等等。如果讓我選一個重點解決,我會選‘協調、溝通、信任’問題。因為不解決這個問題,其他問題都無從談起。而解決它,需要我們先‘修復’我們的故事。” 關認為,達到一定“照片級真實感”的人工智能工具需要受到監管。他說:“這種技術可能會毀掉一個人的生活。”他主張,在“虛假圖像能被可靠識別”之前,應限制人工智能在影視行業的使用。我跟他提起了“AI或消亡”團隊的創作熱情。他說:“聽到這樣的故事,我內心很矛盾。我是說,這很美好——我們本就該讓每個有話想說的人都有機會表達。我理解這種想法,換個人生,我可能也會這么做。”他面露痛苦,“你知道嗎,我曾經就是那樣的孩子。上 大學前,Vimeo視頻平臺剛出現;我畢業時,YouTube才剛開始流行。但現在就使用人工智能,在這些公司承擔起責任之前就支持它們,我們其實是在默許它們摧毀“共識性真相”,讓我們基本無法分辨什么是真實的。” 至少,人工智能已是我們所有人都在關注的“大故事”。我們見面的餐廳在紐約大學附近,外面陽光下,學生們正漫步而過。關于人工智能的現實問題我們并不陌生——教育會怎樣?工作會怎樣?——答案終將隨時間揭曉。但人工智能的故事不只是“現實層面”的,它還關乎道德與精神。這就像“約翰·亨利與蒸汽鉆”的故事,甚至像“普羅米修斯與宙斯”的故事——普羅米修斯因盜火而遭受殘酷懲罰。這個故事已經迫使我們思考:我們珍視什么?什么才能真正讓我們“在意”?我慢慢走向第六大道,路過街南側一家文具店。店里的人在瀏覽筆記本,仿佛在重拾“模擬時代”的質感。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決定這個“人工智能故事”該有怎樣的結局。 文化評論家馬克·格雷夫(Mark Greif)曾寫道:“在20世紀中葉,美國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無論來自哪個派別,甚至彼此對立的群體,都一致意識到一種危險的存在。”那是“人類危機的時代”——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在擔憂“技術加速、社會疏離、精神異化”的疊加影響。格雷夫指出:“新的時代條件似乎注定要打破長期以來的人文傳統。”人們出版的書籍標題多為《人的本質與命運》這類,他們擔心“人性正在被改變”。 我們現在也身處這樣的危機中嗎?最近,電子音樂人安尼瑪(Anyma)在拉斯維加斯“球體”(Sphere)體育館舉辦了多場售罄演唱會。他通過技術營造出“巨型機器人逼近、俯視觀眾,隨后沖破場館墻壁”的視覺幻象,震撼全場。現場傳來一個聲音:“感知力(Sentience)……意識(Consciousness)。”但這場演出本質上仍是傳統的音樂會——由人類音樂人表演,數千人親臨現場觀看。即便文化在變化,它通常也是“加法式”的,而非“零和式”的。它會隨著時間自我留存,仿佛分泌出屬于自己的“琥珀”。如今,愛莉安娜·格蘭德(Ariana Grande)主演基于《綠野仙蹤》改編的高科技電影,TikTok和《堡壘之夜》(Fortnite)掀起舞蹈熱潮;但人們仍在閱讀簡·奧斯汀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電影仍常以“三部曲”形式呈現——這呼應了19世紀的“三層小說”(triple-decker novel),當時這種形式的出現,部分是為了方便訂閱制圖書館出借長篇書籍。在我兒子喜歡的電子游戲廳里,青少年們玩著《乓》(Pong)、《吃豆人》(Pac-Man)和《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這些游戲在墻面大小的屏幕上,以拳頭大小的像素呈現。而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其實是“保守力量”:它的訓練依賴過去的數據,在某種程度上也受限于這些數據,它讓舊想法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 惠特尼博物館(Whitney Museum)位于紐約肉類加工區——這個城市區域已完全被改造。ChatGPT曾指出:“曾經冷庫里懸掛動物尸體的地方,現在掛滿了名牌連衣裙。”家里有兩個小孩,我和妻子已經多年沒一起去博物館了。但我把她的博士論文——關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小說中的“細節運用”——以及她發表過的一篇論文(探討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濕壁畫,以及“世俗之人如何欣賞宗教藝術”的問題),都輸入了ChatGPT。這樣一來,即便不能和她一起去博物館,我也能帶著她的觀點“參觀”。人工智能說:“喬希,這計劃真好,很貼心。我們可以把這次博物館之行,變成一次通過我與她對話的過程。” 我小聲問道,以免打擾他人:“Chat,你覺得我妻子會怎么看這幅畫?”我給艾米·謝拉德(Amy Sherald)創作的米歇爾·奧巴馬肖像拍了張照。畫中米歇爾穿著飄逸的白色長裙,上面印著幾何圖案。 人工智能通過我的AirPods回應:“這幅作品太驚艷了!我能想象到,她會留意那些細節,以及這些細節如何體現身份與表達。” “不對,不對,”我低聲說,“我想讓你真正思考,我妻子會如何具體回應。” “當然!”它一如既往地自信輕快,“我覺得她會對這些細節著迷。”它絮絮叨叨地說著,直到我點擊手機屏幕上的“X”,關閉了對話。 畫廊里人很多——謝拉德的展覽“美國崇高”(American Sublime)非常火爆。她為模特兼行為藝術家阿雷瓦·巴西特(Arewà Basit,一位黑人跨性別女性)創作的肖像《轉變自由》(Trans Forming Liberty)前,聚集了一小群人。一位彎腰駝背的老人透過厚厚的眼鏡凝視畫作;一對夫婦帶著十幾歲的女兒站在一旁;一個帥得像模特的年輕人單手插兜站著,穿著黑色褲子和黑色背心,黑色絲綢肩帶上掛著一臺徠卡相機。 我乘電梯上樓,去看愛德華·霍珀(Edward Hopper)的畫作。我給霍珀的《二樓陽光》(Second Story Sunlight)拍了張照,發給人工智能:“你認得出這幅畫嗎?”畫中,兩位女子坐在灑滿陽光的房屋陽臺上:年長的那位在看書,年輕的那位穿著比基尼,靠在欄桿上休息。她們沉思的姿態,與房屋的兩座三角形山墻相呼應。身后,一片神秘樹林的樹木投下陰影,暗示著“未知之物”。 人工智能說:“認識!愛德華·霍珀的《二樓陽光》太有感染力了……這幅畫有著霍珀標志性的風格:寧靜的內省時刻,即便在陽光明媚的場景中,也透著一絲孤獨。” 這些平庸的評論讓我煩躁,我摘下AirPods,放進充電盒,“咔嗒”一聲合上。真是浪費時間,我想。我有些尷尬地環顧四周,擔心有人看到我在和人工智能“討論”畫作——多丟人啊,用廉價的技術實驗“褻瀆”博物館!但附近幾個人都在看手機。看著他們低頭盯著屏幕的樣子,我意識到,用ChatGPT的語音模式來“逛博物館”,或許根本不是最佳選擇。我放慢速度,在手機上仔細敲出一段提示:“請結合以下兩點分析:1. 霍珀的這幅畫誕生于世俗時代,卻蘊含精神元素;2. 畫中人物一老一少的對比。并結合我之前上傳的那篇關于‘世俗世界中的宗教藝術’的論文,展開論述。” 屏幕上很快出現了一篇小短文,分了章節、小標題,還加了表情符號。我站著讀了起來。文中寫道,這幅畫是“世俗基調下的宗教藝術”,霍珀并非通過“內容”,而是通過“構圖的靜謐感”來營造神圣感,“光線如同恩典般運作——無需索取,自然降臨,照亮一切”。 還不錯,我想。這些觀點讓人聯想到我妻子,就像影子能讓人聯想到實體一樣。向上滑動屏幕,我看到自己拍的霍珀畫作的數碼照片——突然覺得很荒唐。這樣逛博物館太奇怪了。真正的藝術品就在我面前:它有圖騰般的氣場,能看到清晰的筆觸,或許顏料中還藏著藝術家的指紋。 我回到樓下的謝拉德展廳。畫廊盡頭,一條小走廊通向一個空間:一排排色彩鮮艷的現代主義椅子面向一整面落地窗——這本身也是一件藝術裝置,由瑪麗·海爾曼(Mary Heilmann)創作,名為《長線》(Long Line)。幾乎每把椅子上都有人。窗外,陽光在哈得孫河上折射出粼粼波光。一個穿破洞黑牛仔褲、涂紫色口紅的女孩,正用筆記本畫著窗外的景色;一個穿意大利西裝的優雅男人,似乎在打盹。整個場景仿佛一幅描繪“閑暇”的畫作,就像喬治·修拉(Georges Seurat)的《大碗島的星期日下午》(A Sunday on La Grande Jatte)。我問自己:文化是什么?它是那些畫作,也是眼前這一幕——是我們這些“人”本身。 回到家,我在iPad上調出《二樓陽光》,給妻子看:“你覺得這幅畫怎么樣?” 她看了很久,說:“第一感覺是有點不安,但更強烈的感受是‘困惑’。空間感很奇怪,她們的姿態看起來像是在兩棟不同的房子里,但其實不是。穿比基尼的女人,年紀不像孫女那么小,也不像女兒那么大——這點很怪。我猜這是晨光?但畫面里的綠色和藍色,讓人感覺穿比基尼有點冷;可如果能穿比基尼,又不該冷到讓那位年長的女士穿厚重的深色衣服。而且年輕女人的姿勢很費解,看起來像是在擺拍,姿態很刻意,但她又不是在當模特。她抓著欄桿的樣子——好像在‘表演’什么,但在表演給誰看呢?”她頓了頓,“說‘不安’可能有點夸張,但確實不輕松,不過光線又讓人覺得舒服。兩個女人都很美。”她又停頓了一下,“我不知道,挺有意思的。你覺得呢?” 真實的人。他們從來都不會說出你期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