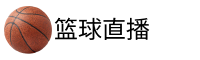Computer scientist Geoffrey Hinton: ‘AI will make a few people much richer and most people poorer’
“人工智能教父”談人類“唯一的希望”、中國何以具備優(yōu)勢——以及機器何時將超越人類。
2025年9月5日

© 詹姆斯·弗格森
我提前了10分鐘到達,杰弗里·辛頓卻已在多倫多里士滿車站酒店(一家雅致的美食酒吧)的前廳等候。這位計算機科學(xué)家——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先驅(qū)、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得主——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他曾在這里與當(dāng)時的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共進午餐。
我們穿過一個裝修風(fēng)格偏工業(yè)風(fēng)、頗具時尚感的葡萄酒吧,來到熱鬧的里間,這里早已坐滿了食客。辛頓取下那個略顯陳舊的綠色“谷歌科學(xué)家”背包(來自他曾任職的公司),由于長期受背傷困擾,他把背包墊在身下,以便坐得更直。
他有著像貓頭鷹般的神態(tài),白發(fā)塞在眼鏡框下方。他低頭看著我,問我在大學(xué)學(xué)的是什么專業(yè)。“因為如果對方擁有理學(xué)學(xué)位,你解釋事情的方式就得不一樣。”我并沒有理學(xué)學(xué)位。不過至少特魯多“懂微積分”。
這位被稱作“人工智能教父”的學(xué)者,早已習(xí)慣向他人講解自己畢生的研究——如今這項研究正逐漸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他見證了人工智能從學(xué)術(shù)界(他幾乎整個職業(yè)生涯都在學(xué)術(shù)界度過,其中在多倫多大學(xué)任職超過20年)走向主流:資金雄厚的科技公司渴望觸達消費者與企業(yè),為人工智能的普及注入了動力。
辛頓因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的“基礎(chǔ)性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獲得諾貝爾獎,這些成果為“基于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的機器學(xué)習(xí)”奠定了基礎(chǔ)。這種方法大致借鑒了人類大腦的工作原理,為我們?nèi)缃裼|手可及的強大人工智能系統(tǒng)打下了根基。
然而,ChatGPT的問世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工智能發(fā)展熱潮,讓辛頓停下了腳步。他不再推動這項技術(shù)加速發(fā)展,而是開始警示其潛在風(fēng)險。過去幾年,隨著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飛速進步,辛頓的態(tài)度變得愈發(fā)悲觀,他指出這項技術(shù)可能會給人類帶來嚴(yán)重危害。
“借助人工智能的普通人,很快就能制造生物武器,這太可怕了。試想一下,如果街上隨便一個普通人都能制造核彈,后果會怎樣?”
在兩個小時的午餐時間里,我們的話題廣泛:從核威脅(“借助人工智能的普通人,很快就能制造生物武器,這太可怕了。試想一下,如果街上隨便一個普通人都能制造核彈,后果會怎樣?”),到他自己使用人工智能的習(xí)慣(稱其“極其有用”),再到聊天機器人如何意外成為他上一段戀情破裂中的“第三者”。
不過,辛頓首先興致勃勃地開啟了一場小型“研討會”,解釋為何“人工智能”是一個恰當(dāng)?shù)男g(shù)語:“無論從何種定義來看,人工智能都是具備智能的。”注意到面前的我是人文社科專業(yè)出身,他用了六七個不同的類比,試圖讓我相信人工智能對現(xiàn)實的感知與人類并無太大差異。
“在我看來,這很明顯。如果你和這些人工智能系統(tǒng)對話、向它們提問,會發(fā)現(xiàn)它們是能理解的,”辛頓接著說,“在技術(shù)領(lǐng)域,幾乎沒人懷疑這些系統(tǒng)會變得越來越智能。”
服務(wù)員過來致歉,打擾了我們的談話。辛頓沒有點葡萄酒,而是選擇了氣泡水而非自來水,理由是“這次由《金融時報》買單”,并提議點套餐。我點了西班牙冷湯作為前菜,主菜選了三文魚。他毫不猶豫地跟我點了一樣的,笑著說其實自己“本來想點些不一樣的”。
辛頓在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業(yè)內(nèi)仍有一些人認為現(xiàn)有技術(shù)不過是一種復(fù)雜的工具。例如,他的前同事、圖靈獎共同得主楊立昆(Yann LeCun)(現(xiàn)任Meta公司首席人工智能科學(xué)家)就認為,支撐ChatGPT等產(chǎn)品的大型語言模型存在局限性,無法與物理世界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在這些懷疑者眼中,這一代人工智能不具備人類智能。
“我們對自身思維的了解其實非常有限,”辛頓說,但對于人工智能系統(tǒng),“是我們創(chuàng)造了它們、構(gòu)建了它們……我們對其的理解程度遠超對人類大腦的理解,因為我們清楚每個‘神經(jīng)元’在做什么。”他說話時充滿篤定,但也承認存在許多未知。在整個交談過程中,他并不介意長時間陷入思考停頓,最后常以“我不知道”或“沒頭緒”收尾。
1947年,辛頓出生于倫敦西南部的溫布爾登,父親是昆蟲學(xué)家,母親是教師。在劍橋大學(xué)國王學(xué)院就讀時,他曾輾轉(zhuǎn)多個專業(yè),最終本科選擇了實驗心理學(xué),并在20世紀(jì)70年代初轉(zhuǎn)向計算機科學(xué)。盡管在21世紀(jì)10年代硅谷接納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之前,該領(lǐng)域一直被計算機科學(xué)界忽視和否定,但辛頓始終堅持對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的研究。
交談中不難發(fā)現(xiàn),他與如今運用他研究成果的人截然不同。辛頓深耕學(xué)術(shù)界多年,而薩姆·奧爾特曼(OpenAI首席執(zhí)行官)卻從斯坦福大學(xué)輟學(xué),專注于創(chuàng)業(yè);辛頓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其成就遲至晚年才得到廣泛認可;而馬克·扎克伯格(Meta創(chuàng)始人)23歲就成為億萬富翁,與社會主義理念相去甚遠。
我們喝著湯時,餐廳里嘈雜的聲音與辛頓輕聲卻嚴(yán)肅地談?wù)撊祟惿鎲栴}的氛圍形成了刺耳的反差。他熱切地闡述了人類如何應(yīng)對現(xiàn)代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部分風(fēng)險——這些系統(tǒng)由“雄心勃勃且極具競爭性的人”開發(fā),他們將人工智能視為未來的個人助手。這聽起來似乎并無危害,但辛頓并不這么認為。
“如果助手比你聰明得多,你該如何保持對它的掌控力?目前我們所知的‘高智能生物被低智能生物掌控’的案例只有一個,那就是母親和嬰兒……如果嬰兒無法掌控母親,就無法存活。”
辛頓認為,人類“唯一的希望”是將人工智能設(shè)計成“人類的母親”,“因為母親會極度關(guān)心嬰兒,保障嬰兒的生命安全”,并助力其成長。“這正是我們應(yīng)該努力構(gòu)建的(人與人工智能的)關(guān)系。”
“這可以作為你文章的標(biāo)題,”他笑著指了指我的筆記本說道。
他告訴我,他之前的博士生伊利亞·薩茨凱弗認同這種“母子關(guān)系”的觀點。薩茨凱弗是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OpenAI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此前因試圖罷免首席執(zhí)行官薩姆·奧爾特曼失敗而離開OpenAI,目前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安全超級智能”公司開發(fā)相關(guān)系統(tǒng)。我問他,奧爾特曼和埃隆·馬斯克(特斯拉CEO)誰更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勝出。他回答:“嗯,不好說。”那在這兩人中,他更信任誰呢?
他停頓了許久,隨后回憶起2016年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被問及在總統(tǒng)候選人中選擇唐納德·特朗普還是特德·克魯斯時說的話:“這就像在‘被槍殺’和‘被毒死’之間選一個。”
說完這話,辛頓提議換到更安靜的地方。我試圖引起服務(wù)員的注意——他們正忙著招待滿座的客人。沒等我開口,他突然站起來開玩笑說:“我去跟他們說,就說我之前和特魯多一起來過這兒。”
我們最終在門口的吧臺高腳凳上坐下,接著討論人工智能何時會發(fā)展到“超級智能”階段——屆時它可能具備超越人類的能力。“很多科學(xué)家認為,最有可能的時間范圍是5到20年。”
我們的菜單
氣泡水(2杯) 6加元
套餐(2份) 98加元
- 庫克鎮(zhèn)西班牙冷湯
- 不倫瑞克三文魚
草莓奶油(2份) 20加元
卡布奇諾 7加元
英式早餐茶 4加元
總計(含稅費) 152.55加元(約合110.65美元)
盡管辛頓對自己的命運有著清醒的認知——“我已經(jīng)77歲了,反正生命也快走到盡頭了”——但許多年輕人可能會因他對未來的看法而感到沮喪。這些年輕人該如何保持樂觀呢?
“我很想說‘他們?yōu)槭裁匆3謽酚^?’或許不那么樂觀,他們反而會做得更多。”他用一個問題回答了我的問題——這是他常有的習(xí)慣。
“假設(shè)你通過望遠鏡看到外星人將在10年后入侵地球,你會問‘我們該如何保持樂觀’嗎?不會的,你會問‘我們到底該怎么應(yīng)對’。如果‘保持樂觀’意味著假裝危險不會發(fā)生,那人們根本沒必要樂觀。”
辛頓對西方政府的干預(yù)并不抱希望,他還批評美國政府缺乏監(jiān)管人工智能的意愿。而白宮則表示,必須加快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事實上,辛頓剛從上海回來,還帶著時差,此前他在上海與中方人士舉行了會談。中方邀請他討論“人工智能帶來的生存威脅”。
“中國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很多政界人士是工程師出身,他們對人工智能的理解,是律師和商人無法比擬的,”他補充道,“對于生存威脅這類問題,只要有一個國家找到解決辦法,就能告訴其他國家。”
“如果助手比你聰明得多,你該如何保持對它的掌控力?”
我們能信任中國會維護全人類的利益嗎?“這是次要問題。人類的生存比‘一切向好’更重要。你能信任美國嗎?你能信任馬克·扎克伯格嗎?”
此時,我們點的三分熟三文魚(鋪在甜玉米濃湯上)上桌了,話題也轉(zhuǎn)向了科技公司開發(fā)人工智能的動機。辛頓一邊說著,一邊用叉子叉起一塊三文魚,在盤子里蘸滿醬汁。
他此前曾呼吁暫停人工智能發(fā)展,并在多封反對OpenAI轉(zhuǎn)型為營利性公司的信上簽名。目前,馬斯克正通過一場尚未了結(jié)的訴訟,試圖阻止OpenAI的這一轉(zhuǎn)型。
人們常說,對人工智能能力的渲染不過是科技公司為推高估值而制造的噱頭,但辛頓認為,“一種說法可能對科技公司有利,同時也可能是事實”。
我很好奇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經(jīng)常使用人工智能。事實證明,ChatGPT是他的首選,主要用于“研究”,但也會用它來查詢諸如“如何修理烘干機”之類的問題。不過,這款聊天機器人還意外卷入了他上一段持續(xù)數(shù)年的戀情中。
“她讓ChatGPT寫了我有多‘渣’,”他坦言,當(dāng)時這個舉動讓他很意外,“她讓聊天機器人羅列我的行為有多糟糕,然后把內(nèi)容發(fā)給了我。我并不覺得自己有多渣,所以也沒太往心里去……后來我遇到了更喜歡的人,你懂的,感情就是這樣。”他笑了笑,接著說:“或許你還沒經(jīng)歷過這種事!”
我克制住了想聊自己過往感情經(jīng)歷的沖動,轉(zhuǎn)而提到我剛慶祝完結(jié)婚一周年。“希望你暫時不會遇到這種感情問題,”他回應(yīng)道,我們都笑了起來。
辛頓吃飯速度快得多,所以當(dāng)他接到姐姐的電話時,我松了口氣。他告訴姐姐,自己正在“一家非常吵的餐廳”接受采訪。他的姐姐住在塔斯馬尼亞(“她很想念倫敦”),哥哥住在法國南部(“他也想念倫敦”),而辛頓住在多倫多(當(dāng)然,他也想念倫敦)。
“所以我用從谷歌賺的錢,在(漢普斯特德)希斯南部買了一棟小房子”,他的家人——包括兩個從拉丁美洲收養(yǎng)的孩子——都可以去那里團聚。
辛頓的“谷歌收入”源于2013年出售一家公司的交易。當(dāng)時,他與薩茨凱弗以及另一名博士生亞歷克斯·克里澤夫斯基共同創(chuàng)辦了這家公司,開發(fā)出了一套能以“人類水平”識別物體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這筆交易的成交價為4400萬美元。辛頓本想三人平分這筆錢,但他的學(xué)生堅持讓他拿40%。交易完成后,他們都加入了谷歌——辛頓在那里工作了10年。
他出售公司的動機是什么?為了給患有神經(jīng)多樣性障礙的兒子支付護理費。辛頓“當(dāng)時估算,大概需要500萬美元……而這筆錢靠學(xué)術(shù)界的收入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他在心里算了筆稅后收入賬,發(fā)現(xiàn)從谷歌獲得的錢“剛好略多于”這個目標(biāo)。
2023年,他離開了這家科技巨頭,并接受了《紐約時報》的采訪,警示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風(fēng)險。當(dāng)時有媒體報道稱,他辭職是為了更坦誠地談?wù)撊斯ぶ悄艿娘L(fēng)險。
“每次接受記者采訪,我都會糾正這個誤解,但從來沒用,因為‘辭職發(fā)聲’是個很有話題性的故事,”他說,“我離開谷歌是因為我已經(jīng)75歲了,編程能力大不如前,而且網(wǎng)飛(Netflix)上還有很多我沒來得及看的劇。我努力工作了55年,覺得是時候退休了……而且我想,反正都要離開了,不如趁機談?wù)勅斯ぶ悄艿娘L(fēng)險。”
科技公司高管們常常描繪一幅“人工智能烏托邦”的圖景:未來,人工智能將幫助解決饑餓、貧困、疾病等重大問題。辛頓的兩任妻子都因癌癥去世,因此他對人工智能在醫(yī)療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前景感到興奮;教育也是他十分關(guān)心的領(lǐng)域,同樣讓他充滿期待,但除此之外,他對人工智能在其他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興趣不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性時刻: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正在發(fā)生,它可能帶來不可思議的好處,也可能造成不可思議的危害。”
“實際情況會是,富人會利用人工智能取代勞動者,”他說,“這將導(dǎo)致大規(guī)模失業(yè),同時企業(yè)利潤大幅上升。最終,少數(shù)人會變得極其富有,而大多數(shù)人會變得更貧窮。這不是人工智能的錯,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
奧爾特曼等科技高管此前曾提議,如果勞動力市場規(guī)模縮小到無法容納全部人口,可推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但辛頓認為,這一制度“無法解決人的尊嚴(yán)問題”,因為人們會從工作中獲得價值感。他坦言,自己很想念以前和博士生一起探討想法、請教問題的時光——“他們年輕,理解事情更快”。如今,他會轉(zhuǎn)而向ChatGPT提問。
這會不會導(dǎo)致人類變得懶惰、缺乏創(chuàng)造力?目前,“認知卸載”是一個熱門話題,指的是人工智能使用者將任務(wù)交給機器,而不進行批判性思考,也不記憶獲取的信息。對此,辛頓又用了一個類比來解釋。
“我們穿衣服,因為穿衣服,體毛變得更少了。如果不穿衣服,我們更容易凍死。”在辛頓看來,只要能獲取有用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它就是一種有價值的工具。
他看了看甜點菜單,這次特意先點了單:草莓奶油。巧合的是,這也是我想吃的。他點了一杯卡布奇諾,我則點了一杯茶。“這下我們的選擇不一樣了。”
事實上,甜點里的“奶油”是略微融化的冰淇淋,我一邊用勺子攪拌著化成液體的冰淇淋,一邊向他描述了一個在硅谷常見、但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仍像科幻故事的場景:未來,我們將與“實體人工智能”(即機器人)和諧共處,同時通過為身體植入人工部件、注射化學(xué)物質(zhì)來延長壽命,逐漸變成“賽博格”(半人半機器)。
“這有什么不好的?”他問道。我反駁說,這樣我們會失去自我認知,忘記“做人的意義”。“‘做人的意義’就那么好嗎?”他回應(yīng)道。我試圖進一步追問:“這不一定是‘好’,但我們將不再擁有‘人性’,這本質(zhì)上不就是人類的滅絕嗎?”
“嗯,你說得有道理,”他停頓了一下,說道。
“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fā)生什么,完全沒頭緒。那些告訴你未來會怎樣的人,都是在瞎扯,”他補充道,“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性時刻: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正在發(fā)生,它可能帶來不可思議的好處,也可能造成不可思議的危害。我們可以猜測,但現(xiàn)狀絕不會一直持續(xù)下去。”
本文作者:克里斯蒂娜·克里德爾是英國《金融時報》科技記者,駐舊金山,主要報道人工智能領(lǐng)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