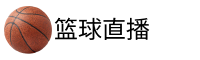9月5日,美國AI巨頭Anthropic發布了一則《更新對不受支持地區的銷售限制》公告,再度聚焦中國市場,明確宣布立即停止向“多數股權由中國資本持有的集團或其子公司”提供Claude人工智能服務,政策還涵蓋在境外注冊的中資子公司、云服務中轉實體等。
早在2024年5月,Anthropic就曾有條款表示不對中國地區開放服務。本次規則是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封殺不局限于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地區,而是對于其認定的中資實體,無論其注冊地是否位于中國,均一律禁止使用Anthropic旗下產品Claude的服務權限。
Anthropic此舉不僅是中美科技戰的最新縮影,其創始人Dario Amodei的從業履歷也引發了眾人的關注。很多人并不知道,Dario Amodei職業生涯的起點是一家中國公司——百度。
從中國公司員工到封殺中國,Dario到底經歷了什么?
從醫學博士后到百度人
作為與OpenAI分庭抗禮的AI巨頭Anthropic的創始人,Dario Amodei在大學期間并未學習計算機及AI相關內容。
Dario原本就讀于斯坦福大學物理系本科,但其父親因患有一種罕見病,于2006年不幸去世。
受此影響,Dario決心棄理從醫,將研究生研究方向從理論物理轉向生物學,實現解決人類疾病難題的愿望。而就在他學習期間,其父親所患病癥取得了重大醫學突破,治愈率從不到50%上升到95%,更是堅定了他從事醫學的決心。
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2011年至2014年,Dario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進行博士后研究,主要聚焦質譜技術在細胞蛋白質組網絡模型及癌癥生物標志物探尋方面的運用。
命運的齒輪如何轉動,才能讓一個醫學高材生轉行搞AI?這就不得不提到當年百度在AI領域的布局了。
2013年7月,百度深度學習研究院(IDL)成立,李彥宏任院長,余凱出任常務副院長。
IDL的成立可以被認定為百度“ALL in AI”的起點。
2014年5月,在余凱的力薦下,AI大牛吳恩達加入百度,同期百度成立了百度硅谷人工智能實驗室(SVAIL),由吳恩達領導,并以優厚條件廣納賢才。
在吳恩達SVAIL的團隊成員中,人工智能專家Greg Diamos(現人工智能企業La Mini創始人)作為團隊核心成員,承擔著招兵買馬的任務,其偶然間看到了Dario Amodei在斯坦福大學期間編寫的代碼,對其質量贊嘆不已。
盡管他沒有科班履歷,也沒有行業頂級論文加持,但是這個年輕人在項目中展現出來的建模功力打動了Greg Diamos。
他評價稱:“能寫出這些代碼的人,一定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程序員”,基于這種欣賞,Greg將Dario推薦給百度,促使其在2014年11月成功入職百度。
在百度摸到Scaling Law門檻
來到百度的Dario并沒有從事其醫學老本行,而是All in AI。
當時,百度硅谷研發中心正在大量招兵買馬,旗下的硅谷人工智能實驗室也引來Facebook前科學家徐偉、AMD架構師吳韌、Twitter數據中心專家Ali Heydari等一批行業大牛的加盟,百度也馬不停蹄地開啟了項目的研究。
Dario在百度參與的是Deep Speech 2,一款語音識別項目。他在復雜系統建模上的學術能力能夠自然遷移到神經網絡的建模與算法優化中,助力語言及語音處理模型構建。
Deep Speech 2在當時發布后可謂遙遙領先,不僅在識別進度上超過谷歌、蘋果、微軟、Facebook等公司競品10個百分點以上,其短語識別詞錯率已降至3.7%,并在2016年入選《麻省理工評論》年度十大突破技術。
相比起這個產品本身,這段研發經歷對于Dario Amodei有著更加重要的啟示。
他曾表示,在百度做語音研究期間,他們已非正式地察覺到了只要為模型供給越多數據、算力,對其訓練越充分,模型性能就越優。
他的這番總結,在如今有個更加熟悉的稱呼——擴展定律(Scaling Law)。這條經驗公式也成了如今大模型發展的底層邏輯。
也就是說,在百度的職場啟蒙生涯直接讓他看清了AI的未來,而當時只有百度等極少數擁有大量數據的大廠才有機會去探索出這個規律。
2015年10月,Dario選擇離開百度。
對于其為何離開百度,Dario本人并未明言,不過隨著2015年5月余凱離職創業,IDL和SVAIL確有一批人陸陸續續出走。
在離開百度后,Dario前往谷歌加入Google Brain,不久后加入草創期的OpenAI。
根據其自己描述,奧特曼和馬斯克當初的AGI愿景并沒有打動他加入,最終加入OpenAI 是基于公司非營利定位和自由研究氛圍。
憑借在百度和谷歌累積的經驗,他參與負責了GPT-2、GPT-3 的研發。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GPT-2面世時,他就反對完全開源,擔心濫用風險。最終OpenAI選擇“有限開放”,理由正是“潛在惡用”。從此,“AI安全”就成為了他身上最顯著的標簽。
隨后的故事更加為人所知,微軟10億資金投資OpenAI,他代表的部分“安全派”員工和奧特曼為首的“快速商業化”派出現了分歧,并最終分道揚鑣自立門戶。
Dario在成立Anthropic后提出Constitutional AI,用書面憲法規則約束模型,通過AI自評自改(RLAIF)減少人為偏見。Claude模型由此誕生,成為ChatGPT的最大對手。
短短幾年,Anthropic拿到Google、Amazon的數十億美元融資,躋身大模型第一梯隊。
沒有“如果” 的遺憾
Anthropic封殺中國與Dario Amodei在百度的經歷大概并無關聯。市場普遍認為,核心原因是其獲得的美國軍方訂單,迫使其必須與中國劃清界限。
但這一事件卻凸顯出一個遺憾的事實:曾經的百度,本有著極為前瞻性的AI技術眼光和深厚根基。
一個著名的故事是,2012年,“AI教父”、后來的諾獎得主杰弗里·辛頓曾在谷歌、Facebook等國際大廠間引發過一場“拍賣”,百度也是參與者之一,曾開出上千萬美元的天價,但最終辛頓因個人意愿選擇了谷歌。
在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等AI核心領域,百度都積累了大量技術成果,構建了龐大的AI人才團隊,甚至早早摸到了大模型的核心規律。但百度不僅錯過了成為大模型領域全球領跑者的機會,也未能充分留住關鍵人才,令這些人才助力其他企業發展壯大。
以余凱為例,他曾在百度深度學習研究院擔任要職,離職后與同樣來自百度的黃暢共同創立地平線機器人公司,專注為深度神經網絡提供專用計算方案。
此外,諸多從百度離職的人才在其他AI企業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自動駕駛尤其是Robotaxi領域,百度堪稱“黃埔軍校”,比如彭軍和樓天成創立小馬智行;韓旭創辦文遠知行;周光成立元戎啟行;倪凱創辦禾多科技。
而和Dario在百度SVAIL共事過的同事們,如今也有不少成為了行業內響當當的人物。其在百度的同事Sherjil Ozair,成為了OpenAI的初創團隊成員;Deep Speech 2的研發組長Bryan Catanzaro,如今是英偉達深度學習應用研究副總裁;而他親手招聘的實習生Jim Fan,如今也已經成為英偉達具身智能項目的負責人。
人們不禁會想,如果當時百度在內部管理、戰略決策以及人才激勵等方面能夠做出更優選擇,充分發揮自身在數據、技術和人才上的優勢,或許就能率先打造出類似GPT的現象級產品,在全球AI競爭中占據更為領先的地位。
然而,商業競爭的殘酷性就在于沒有“如果”。
事實上,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企業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限制。包括辛頓在內的許多科研天才,都會提及谷歌極其自由包容的工作氛圍和不計成本的投入,OpenAI更是依托美國發達的投融資環境,為天才們提供了非盈利的發展環境。而在中國,無論是科技企業自身的盈利能力,還是資本市場的體量,都讓企業很難下定決心去長期投入一個燒錢項目。而本土人才培養體系的尚不成熟,也讓中國企業不得不去美國開設研發機構,這在人才爭奪上處于天然劣勢。
好在,短短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正在快速補上曾經的短板。